
IC 图
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“大而美”税收和支出法案于7月4日正式签署。该法案涵盖减税、移民政策、医疗保障改革、国防开支及绿色能源调整等核心内容。法案的通过不仅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重大政治胜利,也预示着美国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深刻变革。该法案以程序性突破削弱了参议院的制衡功能,同时倒逼全球金融监管升级,并推动金砖国家本币结算,以应对美国政策外溢引发的结构性挑战。
核心内容与政治逻辑
该法案延续了特朗普政府“美国优先”的核心理念,通过税收、福利、能源三大政策支柱构建保守主义政治叙事,其核心逻辑是通过“劫贫济富”的再分配机制重塑美国社会结构,同时以行政集权突破传统制衡体系。
在税收政策重构层面,法案将2017年《减税与就业法案》(TCJA)中的企业所得税率从35%降至21%的政策永久化。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(CBO)分析,该法案十年内将增加赤字3.4万亿美元(含利息后达4.1万亿美元)。值得注意的是,该政策刻意规避了对中产人群的直接冲击,通过精准定位顶层1%群体制造“税收公平”的政治叙事,实质上是将财政压力转嫁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。
福利体系调整则展现出更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。法案不仅计划在2025年—2034年间削减医疗补助(Medicaid)资金超过9000亿美元,更创新性地引入“工作换福利”机制:要求年龄在19岁—64岁间的福利领取者每月完成80小时的带薪工作,否则将失去医疗补助资格。这一设计表面上以“激励劳动参与”为名,实则将加剧医疗资源分配的“马太效应”。根据凯泽家庭基金会测算,采用“区块拨款”模式的州将首当其冲,超过1000万低收入者可能失去医保覆盖。
能源政策的180度转向构成对拜登政府气候议程的全面清算。法案将逐步取消《通胀削减法案》(IRA)中的清洁能源税收抵免体系。这种政策突变导致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陷入尴尬境地。这种倒行逆施引发欧盟碳边境税谈判的僵局,也促使传统盟友如德国开始重新评估跨大西洋能源合作框架。
共和党通过“预算和解程序”(Budget Reconciliation)推进立法,该程序允许以简单多数(51票)通过财政相关法案,而非通常需要60票的冗长辩论门槛。参议院的冗长议事机制本意是促进跨党派协商,但共和党通过预算和解程序快速推进法案,降低了立法审慎性。此外,共和党通过预算和解程序推动的税收改革和能源政策,虽未直接依赖“少数派权力”,但利用程序漏洞规避了民主党的阻力。耶鲁大学宪法学家布鲁斯·阿克曼曾指出,这种“宪法工程学”正在挑战美国民主的程序韧性。
结构性危机
“大而美”法案将造成美国社会撕裂加剧,制度性矛盾集中爆发。
一是贫富分化恶化。根据CBO分析,收入前10%的家庭未来十年将额外获得约3.1万亿美元减税,而收入最低的10%家庭每年需承担更高税负(相当于收入减少3.9%)。中产家庭(年收入4万—10万美元)虽获得小幅减税(每年500美元—1000美元),但远低于富人受益幅度。法案取消加班费、小费收入征税,并扩大“直通企业”免税范围,但这些措施主要惠及服务业从业者中的高收入群体(如企业主),普通工薪阶层受益有限。
二是医疗体系冲击。CBO预测,法案将导致2034年1180万美国人失去医保资格,其中许多是中低收入群体。例如,残障人士、低收入孕妇等群体或面临保障中断风险。强制性工作要求(每6个月需重新提交证明文件)增加了行政负担,可能导致符合条件者因繁琐流程而放弃申请。
三是中产福利缩水。补充营养援助计划(SNAP)申请者年龄下限从54岁提高至64岁,导致部分中年中产人士(尤其是失业或半退休人群)失去资格。各州需自行承担5%的SNAP成本,贫困州可能进一步削减地方配套资金,加剧低收入和中产家庭的食品保障困境。中产家庭的焦虑情绪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发酵,“生存数学”(Survival Math)话题下,大量用户分享如何用缩减后的补助覆盖房租、通勤和医疗等基本开支,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数字时代抗议形态。
此外,美国经济与财政风险攀升,美元霸权遭遇系统性挑战。
法案预计未来十年增加赤字3.4万亿美元,联邦债务上限提高5万亿美元。尽管短期通过减税刺激消费,但长期债务压力可能通过提高利率、通胀或削减公共服务转嫁至中产家庭。例如,10年期美债收益率或上升1.2个百分点,推高房贷与消费贷利率。更危险的是,债务货币化操作导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膨胀至9万亿美元,严重挤压本应投向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公共资金空间。
市场反应表明美元信用受损:3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.1%,创2007年以来新高;美元指数跌至2022年低位;与此同时,黄金ETF持仓量激增23%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数据显示,2025年第一季度全球央行持有的美债总量下降8%。沙特、巴西等国已启动双边贸易本币结算试点,“去美元化”国家数量不断扩展。
最后,产业与全球供应链重构,新旧秩序的激烈碰撞。
一是新能源产业受挫。法案取消2025年9月后对新购电动车的7500美元联邦税收抵免,并终止二手电动车4000美元补贴。特斯拉、通用等车企年损或超12亿美元,预计2030年电动车销量将较现在减少40%。针对锂、钴等关键矿物的开发支持(如冶金煤抵免)将在2029年后全面终止,迫使美国新能源供应链依赖进口,加剧供应链不稳定性。
二是制造业回流争议。芯片、军工等高附加值产业受政策吸引加速回流,但消费电子等低附加值产业因成本过高难以回归。法案将半导体建厂税收抵免从25%提至35%,吸引台积电、英特尔等巨头加速投资。然而,美国制造业综合成本仍高于亚洲:工人时薪为越南的6倍,土地与物流成本居高不下。即使综合成本降低18%,普通制造业如消费电子仍难以承受。
应对策略
这场围绕法案的激烈争议,深刻暴露了美国政治体系的深层病灶:两党利用“预算和解程序”强行通过争议性法案,规避了常规的立法辩论与协商程序;社交媒体算法制造的信息茧房效应,导致63%的选民主要接触符合自身预设立场的信息。正如《经济学人》指出的那样,美国正经历“民主成本高于民主收益”的关键拐点,这种制度性的衰败,其长期影响与逆转难度,可能远超任何单一的经济危机。
对此,应该加强多边合作应对美元波动。面对美元地位动摇和债务风险上升,主权基金和外汇储备管理者需调整资产配置。可适度减持美债,转向黄金储备、欧元资产及新兴市场优质资产,以分散美元贬值风险,增强自身话语权。同时,金砖国家可加速推进本币结算机制,减少对美元依赖。同时,探索共同开发数字货币,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跨境支付高效与低成本,削弱美国金融压力,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替代性金融基础设施。
另一方面,加强金融监管与风险预警。IMF应加强对美国财政健康状况、债务可持续性及其外溢风险的监测与分析,向成员国发出呼吁,强调外汇储备多元化战略重要性,并提供专业建议,帮助成员国评估和管理与美元资产相关的风险。同时,对资本流动冲击敏感的发展中国家,应积极升级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箱,优化外汇储备结构,完善资本流动管理框架,建立或强化金融风险早期预警系统,监测金融市场动向、汇率压力、外债水平等关键指标,提升预判和快速反应能力,维护本国金融市场稳定。
(作者为赛迪研究院研究员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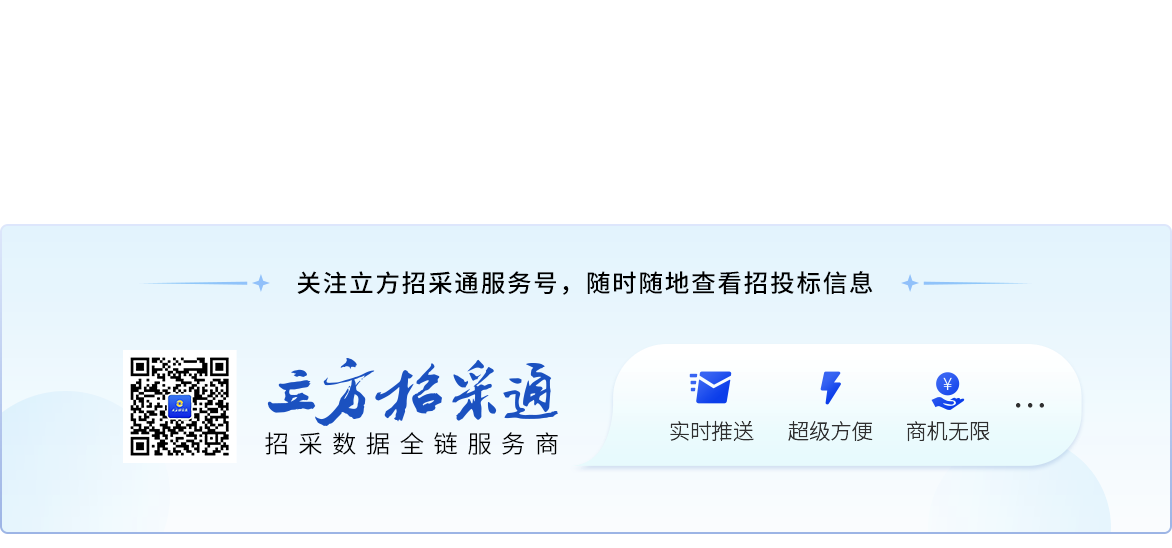

 当前位置:
当前位置:





